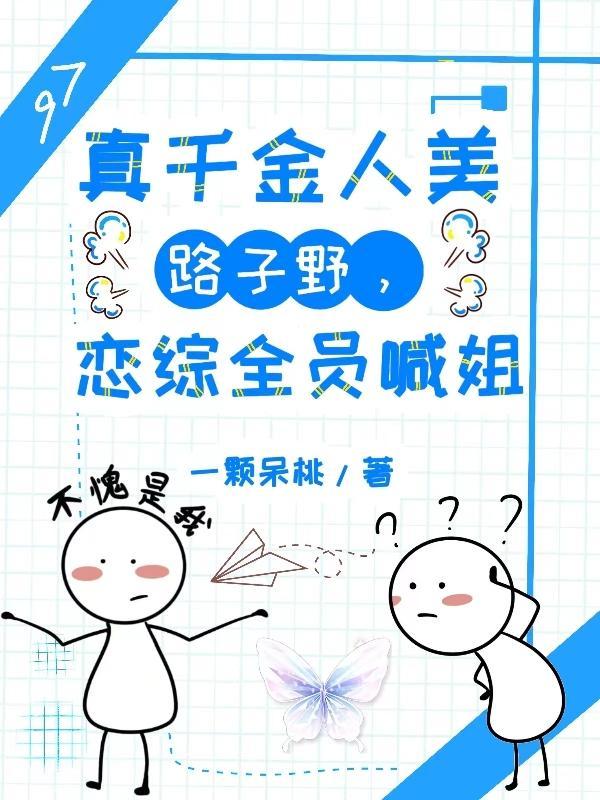乐趣小说>龙血沸腾 > 第二章 开示(第3页)
第二章 开示(第3页)
不知何时,安度兰长老走到了老刘的身后,手中的拐棍敲在刘震撼已然冻结的脑袋上,当头棒喝!
仿佛一阵黄钟大吕,又如天花乱坠地涌金莲,无数絮语的浪花冲入刘震撼心头,熄灭了炽燃的怒火,冲走了掩住双眼的执念。刘震撼只觉得心里从未如此清明,一种明悟如甘泉般涌出,一时也顾不得赤裸娇躯满身精秽的爱妻们,和坐满一地全无反抗之力的熊地精,只是放开喉咙高歌一曲:「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,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,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,粉正香,如何两鬓又成霜?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,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,银满箱,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,那知自己归来丧!训有方,保不定日后作强梁。择膏粱,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!因嫌纱帽小,致使锁枷杠,昨怜破袄寒,今嫌紫蟒长: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,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!」
歌声刚落,一道夹杂着堂皇的金色以及暧昧的粉色的战歌光环应声涌起,笼罩当场,不但把两个还躺在地上意乱情迷的老板娘笼罩在其中,更把刘震撼自己和身边的安度兰长老以及赶过来的海伦笼罩其中。
「虽然不懂你使用的语言,但是这种力量,让我明白了你的意思,解得切,解得切。」
安度兰长老体味着笼罩于身上的战歌光环,「这是战歌光环?似乎有壮阳、催情作用,但是还不仅仅如此,还有什么……」
正在他想着的时候,福克斯少女海伦忽然跪在地上,满脸通红地解着老玳瑁人的袍子,然后直接把一根蓦然耸立的肉枪含入口中。刘震撼看在眼里,却没什么反应,反而是对一个蔫巴老茄子竟然能长出丝毫不亚于自己的「茄子柄」而感到诧异。这根老枪色泽黑紫,嶙峋处若积年老树,在龟头的冠状沟后更生出一圈短粗肉刺,衬得硕大的龟头神似一小号榴莲,煞是狰狞。
「哦哦!」
老玳瑁人忽然按住海伦的头,龟头直接顶进小狐狸的喉咙中,让她眼泪都流了出来,一副欲呕不得的样子。
「这战歌不单能催情壮阳,更能让人一瞬间便达到高潮!」
「哦克哦克!」
那边的熊地精领按着艾薇尔的头,也因为战歌光环的力量,瞬间到达高潮。
然而,在先前纵欲几乎精尽人亡的时候,骤遇心情大起大落,最后又强行被榨出一次,这个熊地精最终捂着胸口抽搐两次,寂然不动,竟然是马上疯,死了!
可是就算他已经死了,胯下的那根鸡巴却傲然挺立在它的尸上,生机盎然。
艾薇尔欣喜地舔舐着龟头上残留的精液,丝毫没有在意这根肉棒的主人其实已经死了。
看到眼前的这一幕,刘震撼没有气愤没有暴躁,反而异常的平静。他嘴里嗫嚅有声,时高时低,念的还是一门没听过的语言。安度兰长老就算站得近也听不清,还是靠菩提圆觉身六神通之一的「他心通」才知晓他念诵的意思:「一个丈夫,毫无利己的动机,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别人的的妻子,这是什么精神?
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,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,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……
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,表现在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性生活极端的负责任,对共产共妻的极端的热忱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。不少的人对同志对人民的性生活不负责任,拈轻怕重,把撸管的工作推给人家,自己搂着老婆学习姿势。
妻子当前,只让自己肏,不让别人肏。肏过两个女人就觉得了不起,喜欢自吹,生怕人家不知道。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,而是冷冷清清,漠不关心,麻木不仁。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,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……
对于渣诚的死,我是很悲痛的。现在大家纪念他,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。
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,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鸡巴有大小,时间有长短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」
当刘震撼默念完的时候,他的眼神异常明亮,视线近乎在燃烧,众多革命导师穿越无数宇宙空间,在此刻灵魂附体,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他不是一个人!
老刘口中低颂的话语渐渐清晰,后来竟然如滚滚雷霆,在歌力的加持下,在场的所有人虽然听不懂他念诵的语言,却也清楚地明白了言语中传达出的坚定信念:「从今天开始,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从今天开始,我的妻子就是大家的妻子,每个人都要尽情享用她们,而我,则要抢过最艰辛的撸管的工作,撸我自己的管,让别人肏我老婆去吧!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,当他回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,在临死的时候,他就能够说:『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,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共产共妻而奋斗。』」听得刘震撼的话,安度兰长老颇为欣慰地点点头,道:「善哉,你已明悟。这个世界即将以你为轴开始转动,你将拥有众多的妻子,这些妻子将成为齿轮,为众生造就无尽福祉。」
「谢谢长老点醒了我,从今开始,您就是翡冷翠的座上宾,我和我的妻子、领民都奉您为师!」
老刘面露狂喜之色,道。
安度兰长老含笑点头,念珠一转,随手点向心脏病突的熊地精领,只见一道金光闪过,熊地精领猛地一颤,一口浓痰卡出,却又活了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