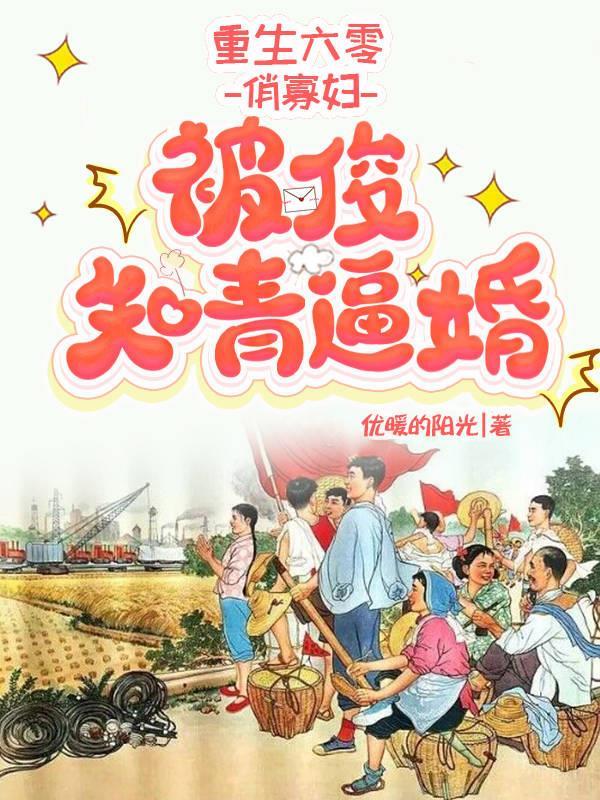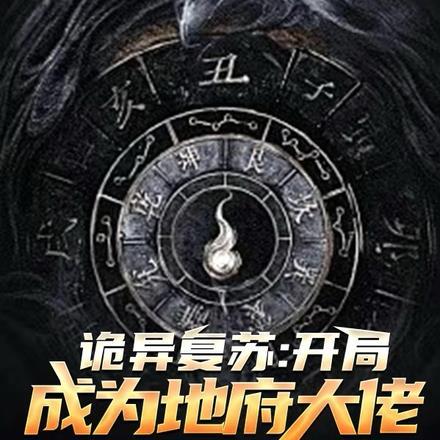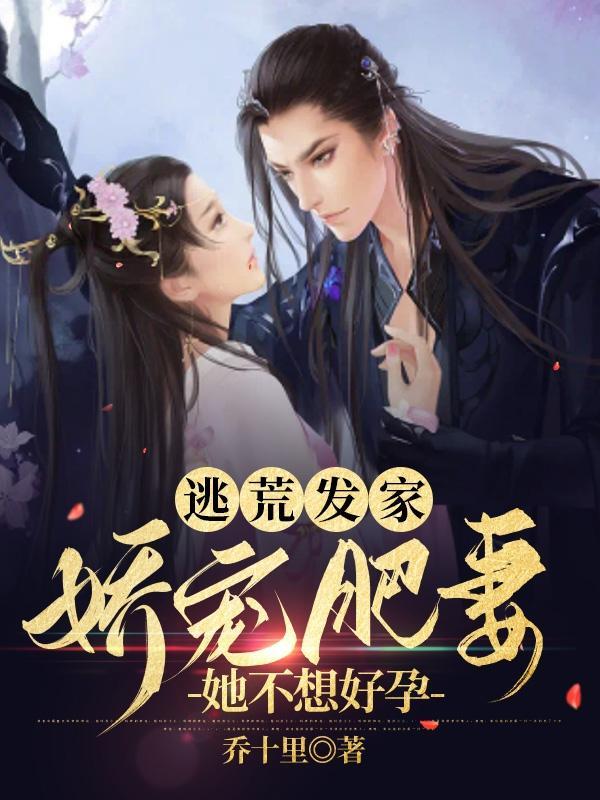乐趣小说>成道天书 > 第251章 由根本论(第2页)
第251章 由根本论(第2页)
从而洞悉道教之展、女性观念之转变,以及对社会所产生之意义等问题。做一个具真我思想之修行者,此实乃重中之重。
据相关史料记载,“女仙”并非道教产生后才出现的。部分道教女仙,实则是源自于,早期神仙家塑造的神女形象,与民间传说而来。
道教将这些神女纳入记载后,根据自身实际需求,改变或重塑其形象,使其成为符合道教教义的“女仙”存在。
其中,较为典型且广为人知的,有“巫山神女”“西王母”等等。“巫山神女”别名瑶姬,亦是道教所说西王母的二十三女“云华夫人”。
在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曾有记载,其本为炎帝之女,本体为仙灵芝(《襄阳耆旧记》亦有相同记载)。
实际上,“巫山神女”是炎帝女儿之事,鲜为人知,人们对她的了解,更多是从宋玉所着的《高唐赋》和《神女赋》中得知。
《文选》卷十九,宋玉《高唐赋》中有言:“妾巫山之女也,为高唐之客,闻君游高唐,愿荐枕席。”
在此记载中,“巫山神女”自称为“妾”、为“客”,甚至自荐枕席,似乎与她尊贵的帝女身份极不相称。然而,呈现给世人的,却是一位大胆、崇尚自由、甚至有些奔放不羁、近乎放荡的神女形象。
所谓抛开全部场景,只讲一点事情,便是在卖弄文化、耍流氓!读书学文、看剧阅览,必须联系时代背景去看待、去思考。
华夏战国时期,思想多元、社会上百家争鸣,意识形态开放,相关礼节约束并不明显强硬。
宋玉所在的楚国,相比中原各诸侯国来说,较为开放,他们喜欢浪漫,尊重男女关系自由,女子出游郊外,游戏青山绿水,纵情山野乃为平常。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宋玉笔下的“神女”于出游中遇到楚襄王,并大胆示爱、自由奔放的行为,就有了现实依据与时代依托。
有人认为,因为“巫山神女”瑶姬之名,本身就含有“淫”之含义,且负有诱导生殖的潜意识功能,所以才表现出了其放荡开放之神女形象。
但其实,不论是神女之名产生,由当时所有何寓意寄,在宋玉笔下的神女,都会被赋予战国时期的,时代特点,以及楚国地域特色。
古籍中所传一切的史前神话,都会掺杂着书者时代器用,以及时代背景。甚至于连宋玉自身的主观认知,也在这大时代背景之下,摆脱不了的!刘向之《列仙传》亦是如此。
相较于《高唐赋》中对“巫山神女”的简略阐述,宋玉后续所着《神女赋》的描述更为完备详尽。
其对神女的容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,以华美的辞藻勾勒出神女的端庄高贵、倾国倾城。
其次,面对楚襄王的殷勤示爱,神女“微嗔以自守兮,绝不可乎冒犯”,继而甩袖离去,展现出冰清玉洁的“贞女”形象。
“巫山神女”从《高唐赋》里的“奔女”蜕变为《神女赋》中的“贞女”,或许能反映出在早期人们尚未受到严苛封建礼教桎梏时,对于性欲之原始欲望敢于袒露、勇于追爱、尊崇婚姻自主等特质。
故而《高唐赋》中洒脱不羁的神女契合当时的社会观念,人们并不觉得其淫荡,作者在创作时自然无需避讳。
然而,随着社会的演进,礼教文明的束缚使得人们不再肆意放纵,对于性欲之原始欲望难以启齿,男女之事、婚姻之事在等级、礼制的桎梏约束下也不再自由。
种种变革,致使《神女赋》中的神女被描绘成一位温婉娴淑、高雅端庄、洁身自好、严守礼教的“贞女”,契合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。
然而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“神女”回绝襄王,让楚襄王求而不得、苦等到天明,似乎也流露出某种政治意味,意在暗示臣子规劝君王不可沉溺于女色。
而后,“巫山神女”被收入《墉城集仙录》时,她已不再是“朝云暮雨”、豪放不羁的神女,亦非美丽高雅、守身如玉的“贞女”,而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、协助大禹治水的“云华夫人”。
杜光庭笔下的巫山神女实现了身份的转换,从多情貌美的神女蜕变成传道济世的女仙,达成了神性与人性的融合。
这深切地契合了道教追求长生、崇拜女仙、降授传道等教义和思想,亦彰显出当时人们在道教思想影响下对生命的美好憧憬。
于此,亦是告诫修行者,切不可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束缚,世间万物变幻无常,必要释放元神,舒缓心境之累,挣脱自我及意识上的无形桎梏,专心朝着道法自然、正心明神合一之境迈进,方为正途。
正因如此,所有有关女仙的故事传说,从最初的“帝女”到战国时期的“神女”,再到道教所记载的“女仙”,巫山神女瑶姬形象的变化,乃是不同时代背景下,不同思想的更迭,亦是人们价值观追求转变的一种映照。
道门之内,“西王母”之名,世人谓之王母娘娘,修真者则尊其为“金母元君”,乃历史上至关重要之女帝级神灵,更是道门所尊崇之大尊神。
关于“西王母”之记载,最早文献所载,当属《山海经》,其中约有三处详实之记录。
其一,于《西次三经》中,西王母“豹尾虎齿”,其为掌管天下刑罚之“凶神”。
其二,于《海内北经》中,西王母“梯几而戴胜”,身侧有三青鸟。
其三,于《大荒西经》中,西王母人面虎身,呈“半人半兽”之态,野性与原始特征尽显。
由《山海经》所记西王母之形象,修者可察,受彼时生活方式及图腾崇拜之影响,人之于神之想象、认知,乃至建构,亦充满野性,近乎自然原始之态。
然随社会之展,及人思想观念之转变,西王母渐脱“凶神”之象,身侧始现象征长生之意之“三青乌”,且常与帝王相联。
西周历史神话典籍《穆天子传》及《汉武故事》《汉武帝内传》《博物志》等,其中所记载的“西王母”故事,多有体现。
穆王西征访王母故事中,“西王母”被塑造成一位擅长吟诗、通情达理的娴雅女性形象。
她仿若一位外族女性领,女神特征不甚明显,除一句“我惟帝女”外,别无其他相关描述。
相较而言,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故事,流传更为广泛,其中对西王母特征的描写亦更为详尽具体。
汉王朝时期,社会上盛行长生不老之思想。汉武帝又好求仙道,在此背景下,西王母之形象,可想而知,深入人心!民间对西王母的崇拜之风盛行,自然成为神话历史之必然。
而现实时空亦如此运转,汉哀帝时期,一场社会危机爆,西王母遂成为“救世主”形象。
据《汉书?五行志》记载,汉哀帝建平四年,生了一次“西王母诏筹事件”。
此次征筹,规模宏大,历时长久,乃一场全国性之崇拜活动。
西王母不仅走下神坛,为凡人赐福、增寿,成为民众信仰之神母,其形象亦由高不可攀之女神,转变为“救世主”,于民众心中之地位,愈凸显。
而有关西王母的故事,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,每一个阶段,皆因时代背景不同和社会观念不同,具有了不同的特点。但总体趋势上,其形象在不断美化、地位愈加得以尊崇。
“巫山神女”与“西王母”两个早期女神代表人物,关于她们的记载表明,虽然“女仙”一词,最早出现于道教文献中,但在此之前,就已有了关于女仙故事的书写描述。
道门接纳这些女神人物,重塑其昔日神话色彩,赋予她们典雅的女仙形象,旨在吸引更多女性修士,入道、修道、成仙、得正位,借此弘扬道门教义、传播道教思想。
道教女仙故事堪称道教神仙信仰的展现,而“西王母神话”更是将道教神仙传的想象力、表现力挥到了极致。
《太平经》亦名《太平清领书》,大致成书于东汉中晚期,乃早期道教经典文献,其所蕴含的性别思想和女性观念,彰显着彼时道教的性别立场。